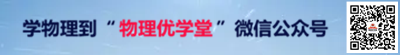
愛有多少種同義詞
漢語中很多詞匯都有近義詞和同義詞,這項“配對技能”,我們在小學(xué)二三年級的時候就已熟練掌握。不過,隨著年歲日增,生活的洪流泥沙俱下,我們便漸漸明白,近義詞很多——比如“希望”約等于“期待”;而同義詞甚少——比如“干凈”不等于“潔凈”“純凈”“素凈”……至于那些純粹的字眼,尤甚。
比如,很難給“愛”找出一個絕對匹配的同義詞。
當(dāng)然以上是在我此行出發(fā)之前的觀念,而它被逆轉(zhuǎn),只用了五天,動搖我固執(zhí)想法的,也都是平凡普通的人。
“愛”=“故事”
有故事就會有矛盾,有矛盾,就會有“壞人”,哪里有什么故事是純?nèi)?ldquo;愛”的?當(dāng)然有,這要看你用什么樣的心去看待它。就以我們此行講了很多遍的苗族故事《獵人果列》為例——
它確實(shí)是一個獵人打老虎精的故事,可是作為“反面人物”的老虎精,卻在一遍遍的講述中變得立體了,真實(shí)了,可愛了。尤其是母老虎精為了招待“遠(yuǎn)房侄子”,又是捉雞,又是煮肉,又是燙酒蒸米飯,活脫脫就是一個在廚房里忙忙叨叨的嬸子阿姨。當(dāng)她發(fā)現(xiàn)“遠(yuǎn)房侄子”不好招惹的時候,第一反應(yīng)就是保護(hù)自己的三個兒子,而當(dāng)孩子們吃了虧,乃至性命攸關(guān)時,她也真的豁出老命去救——這不是每個普通的媽媽都會做的事情嗎?
這些我花了蠻久時間才領(lǐng)悟到的事情,聽故事的小朋友卻完全不含糊。在這個故事里,他們最喜歡的`人物也許是果列,也許是苗族姑娘,但沒有一個小朋友會憎惡老虎精一家子。我想,這大概是因為孩子的眼睛原本就更清亮,并沒有用善惡二元的概念先入為主。
而寫故事的人,原本就是為了描述愛,傳遞愛,他筆下的故事,只要細(xì)讀、深思,都是“愛”的同義詞。
“愛”=“笑”
自從我畢業(yè)工作,就一直在和孩子們打交道,他們的笑容可謂世界上最真實(shí)的東西之一:喜歡你就沖你笑,不喜歡你就不理你。但是在貴定苗寨,我原本以為這樣的笑容里會多少隱藏著一些傷感和自卑,因為孩子們生活的條件實(shí)在太艱苦了:自來水不一定有,電燈暗幽幽的,父母可能不在身邊,也許一年能見一面,也許再也見不到面……什么人能在這樣的環(huán)境里真心微笑?可是這兒的孩子們就是像油菜花一樣笑得燦爛。前一秒還和你很陌生,下一秒已經(jīng)難分難舍,恨不得拉著你去他家住。
也許有人會反駁說,孩子們懵懂不諳世事,沒見過好日子,當(dāng)然什么都能接受。可是他們的兄長、父母、祖輩呢?他們是知道外面的世界的,可是他們的笑容,也同樣真實(shí)純粹,沒摻雜什么“自強(qiáng)不息”“堅韌奮斗”。
他們綻放這樣的笑容,就是因為在對方的言行里感受到了愛。這是一種最原始、卻也最高級的反饋。他們的每一抹笑容,都是“愛”的同義詞。
“愛”=“一餐飯”
臨行前就有很多朋友告訴我,苗族鄉(xiāng)親非常好客,當(dāng)心喝醉爬不起來、吃撐不動路唷。苗族同胞好客我是信的,可那只在電視里見過,而對他們來說,我們是初次謀面的陌生人,再說,時代已經(jīng)變了,人心若是跟著變,也沒什么好奇怪的。
可是到了苗寨,我就發(fā)現(xiàn)自己錯了。且不說來接我們的陳大哥一早啟程,翻山越嶺兩三個小時才趕到機(jī)場,也不說袁光英園長鼎力配合、細(xì)致入微,看我穿得太少還拿來自己女兒的羽絨服,單說我們走在村子里,就沒有看到幾戶人家的大門是鎖著的。
上午在幼兒園里聽過故事的孩子們,叫著“鳥老師,鳥老師”,沒聽過故事的大人見狀便咧嘴一笑,請我們進(jìn)屋坐坐。不知不覺間天色已晚,一家大小拉著鳥老師,拉著工作人員,拉著攝影師,一定要我們在家里吃一頓飯。
于是大鍋燒起來了,臘肉飄著香氣,青菜入了鍋,白花花熱騰騰的米飯送到我們手上……我甚至忍不住默默猜測,會不會連人家的年菜也給吃掉了,可看到他們開心的樣子,卻仿佛比過年還要高興。
“愛”=“執(zhí)著”
我喜歡執(zhí)著的人,因為執(zhí)著代表著有目標(biāo)有夢想,有沖勁兒有堅持。那些別人看起來很傻的事,其實(shí)都是由內(nèi)心的執(zhí)著支撐著的,都是由心靈深處的渴望生發(fā)的。